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把車駛出高速公路,但我很高興自己這麼做了。
因為如此一來,我才走上恢復清晰視力的路,左眼不至於失明。

在射擊職涯步入尾聲時期,我看東西漸漸感覺吃力——甚至嚴重到我學會了制約大腦對著模糊的目標射擊。那時我對正式比賽標靶上的那四英寸黑點真是喜愛不已,它讓我能夠全神貫注在那個中心點。
我從射擊運動中退休之前的兩年,已經無法看清十碼線外的射擊目標。我在二0一七年做了白內障手術;多虧了手術,我的視力比幾年前的更好,看東西一清二楚;顏色也變了,我甚至能分辨出白色冷暖值的差別。可惜好景不常。
一片茫然
我十一歲起就戴有度數的眼鏡,在我從事射擊運動的歲月裡,每年我都做眼科檢查,好跟上眼睛的變化。二0一八年末,在我從射擊競技退休後,視線糊似乎又回來了,我也不知我的視力是否只是隨著年齡而退化。

但事實並非如此。等我去看眼科醫生時,我的左眼已經失去四十%的視力,醫生說這是因為之前的白內障手術而引起。他說,大約二%的白內障手術患者的切口會留下疤痕組織,導致視線模糊。而不幸的是,我就是那二%當中的一個。
醫生說我可以再做一次去疤手術,好再次恢復清楚的視力,一如我上次做過白內障手術之後。
我猶豫不決,不知是否值得冒險一試。我擔心另一次手術意味著另一個傷口,運氣不好的話怎麼辦?我想第二次手術是一種冒險;萬一出了什麼問題,我甚至可能因為手術後出現更多的疤痕很快就失明。若不開刀,左眼的視力起碼可以再維持幾年。一個求精求準的手槍射擊選手若失去一度重要無比的資產,想來有些諷刺,我想還是等我住進養老院之後再做手術比較好。
我一生嚐過很多艱辛,也從中學會了忍耐。當你移民到一個你完全不懂它的語言的陌生國度,會嚐到這種苦;愛子因病夭折、射擊生涯展開之初及整個過程中被人藐視或矮化,個中辛酸更是冷暖自知。
視力受損的挑戰
我也不知怎的就度過了過去的種種挑戰。我想,這一次視力受損,就是我必須忍受的另一個障礙吧。
只是這一次對視力退化逆來順受、讓命運來決定,我犯了一個錯誤,還好那天在去靶場練習散彈槍途中我及時醒悟。無論出於何種原因,我突然感到一種緊迫感,要把車停到路邊、給我的眼科醫生打電話。

我極其相信不能忽視生活中突然出現的各種信號,出自本能的知道不要不管它。因此,我把車停在僻巷,打電話給醫生安排看診時間。
兩周後我赴約看診時,左眼已經失去了大約六十%的視力。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前去就醫只靠一隻好眼睛,有點費勁。醫生告訴我,他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手術除去疤痕組織、改善我的視力。而上次我們看診談話時,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必須做另一個切口,通過手術除掉疤痕。
我約莫是誤會了。這一次,他說他可以用雷射除疤,不會產生更多的疤痕。
即便如此,我當天也沒有準備好接受手術的心理準備。我告訴他,過幾週等我的行事歷活動更有彈性時,我再回來。只是仍有一個問題:我的醫生剛剛決定退休,不行醫了、要去學小提琴。張醫生是眼科的部門主管,過去十二年來一直追蹤我的視力情況。
若要他來動手術,若非現在,只怕永遠沒有機會了。

我與我這位眼科醫生很合得來,我也信任他。我真的不希望由另一位醫生來動手術;而我若是延後,操刀的就會是另一個醫生。
醫生恢復我視力的那一天
我的醫生那天精神飽滿,散發出正能量。我把這看成另一個我不應該忽視的信號。
接受手術,你當然希望自己的醫生處於最佳狀態。很明顯的,我的醫生那天就在最好狀態,我決定必須抓住機會。
手術僅花了幾分鐘。我若是一開始就知道手術如此快速和簡單,絕對不會擔心。手術後,我的視線很不清楚,到了我需要禱告的程度。我視線模糊的開車回到家,睡覺休息。幾個小時後,我再度睜開眼睛時,視力清晰無比。
我一生拒絕向任何所遇挑戰屈服,然而我也試著坦然接受我無法控制之事,不與之相抗。我一直努力保持樂觀,不因生活中的負面事務而下沉。這次經歷提醒了我不要過早接受不能令人滿意的命運;自己要做做功課,在接受之前,看看是否能夠改善情況。福禍安危都是定數,我們都必須抓緊人生,盡可能活得徹底。
我感謝神祗給了我另一個機會讓我保有健康的視力,而我也不視其為理所當然。我知道我需要時刻注意祂如何對我說話,不漠視祂發出的信號。在神祗引領下,我能看得清楚。
Post originally published at 《女性戶外運動新聞》.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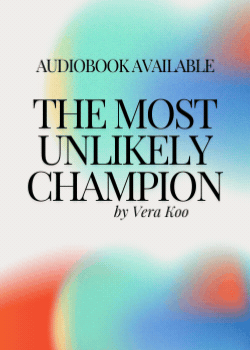
You are absolutely amazing!!!